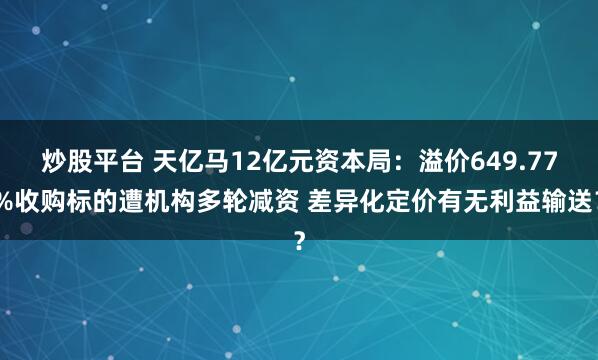那年夏天线上股票配资网址,绿皮火车把我从山里吐出来的时候,整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、正在冒着热气的蒸笼。
空气是粘稠的,混着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化了的甜腥气,还有街边油条摊子散发出的、让人肚子空得发慌的香气。
我捏着口袋里那几张被汗浸得发软的票子,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口,觉得自己的影子都被这水泥地面吸进去了一部分。
工地是老乡介绍的,在城郊。
那地方,白天是机器的轰鸣和漫天飞扬的尘土,晚上是蚊虫的嗡嗡和远处传来的、模糊不清的火车汽笛。
我分到了一把铁锹,锹柄被无数只手磨得光滑油亮,像一件传了代的兵器。
我的任务是拌混凝土。
沙子、石子、水泥,按照工头喊出的比例,一锹一锹地撮进搅拌机里。那机器像一头永远吃不饱的铁胃怪兽,轰隆隆地转,吐出灰色的、浓稠的浆液。
汗水从额头淌下来,流进眼睛里,又涩又疼。我不敢用手揉,手上的水泥干了,会把眼皮搓破。只能用力眨几下,让更多的汗混着泪一起流出来。
工地上的人,说话都像吵架,嗓门扯得老高,不然就会被机器声盖过去。
工头姓王,我们背地里叫他“王阎王”。他总绷着一张脸,像是谁都欠他钱。眼睛像鹰一样,在工地上空盘旋,谁要是手脚慢了半拍,他的骂声就跟鞭子一样抽过来。
“没吃饭啊!动起来!那料都快干了!”
他的声音穿透搅拌机的轰鸣,精准地扎在每个人的耳膜上。
我只是闷头干活。我知道,我没有资格慢。
我爹送我上火车的时候说,到了城里,别惹事,也别怕事,把力气用在正道上。
所以,我把所有力气都用在了那把铁锹上。
每天收工,我的两条胳膊都像灌了铅,抬不起来。躺在工棚的大通铺上,骨头缝里都往外渗着酸。
空气里是浓重的汗味、烟味,还有一种廉价药酒的味道。旁边铺的老哥每天晚上都要用药酒搓腿,那气味,冲得人脑门疼。
但我很快就睡着了。
因为太累了。累到没有力气做梦。
工地的伙食是大锅饭,白菜炖豆腐,豆腐炖白菜,偶尔能看见几片飘着的肥肉,得靠抢。馒头是管够的,但很硬,像石头。
我总是把馒头泡在菜汤里,等它软了,再大口大口地咽下去。那滋味,谈不上好,也谈不上坏,就是一种能填饱肚子的味道。
有时候,我会想起我娘做的手擀面,面汤上飘着翠绿的葱花。
这个念头只敢在心里转一圈,不敢多想。想多了,手里的馒头就更难以下咽。
工地上唯一的亮色,是王工头的女儿。
她叫王静。
她偶尔会来工地送饭,或者送些西瓜。
她来的时候,工地上喧嚣的空气仿佛会瞬间凝固一秒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会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过去。
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,裙摆像一朵安静的云。她的皮肤很白,是那种常年在屋子里待着,没被太阳晒过的白。
在这片被灰色水泥和黄色尘土统治的王国里,她就像一抹凭空出现的、不真实的色彩。
她走路很轻,不像我们,脚踩在地上,一步一个坑。她走过来,像一片羽毛飘过来。
她会把饭盒递给她爹,然后线上股票配资网址站在一边,安静地等着。眼睛会不经意地扫过我们这群光着膀子、浑身泥浆的汉子。
她的眼神里没有嫌弃,只是一种淡淡的好奇,像是在看一幅与她无关的、生动的画。
大多数时候,我都是低着头的。
我不敢看她。
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汗臭和水泥味,会玷污了她身上的那份干净。
有一次,我正埋头用铁锹翻着砂堆,一双白色的凉鞋停在了我面前。
我顺着凉鞋往上看,是她。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她递给我一瓶橘子汽水,瓶身上还挂着细小的水珠,冰凉冰凉的。
“喝吧,解解暑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风吹过树叶。
我愣住了,握着铁锹,不知道是该接还是不该接。
我的手太脏了,满是水泥和沙砾,还有被铁锹磨出的血泡渗出的干涸血迹。
“拿着呀。”她又说了一句,往前递了递。
我窘迫地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手,还是觉得不干净。最后,我用两根手指,小心翼翼地捏住了瓶盖。
“谢谢。”我的声音很干,像被砂纸打磨过。
“不客气。”她笑了笑,嘴角有两个浅浅的窝。
她转身走了。
我握着那瓶汽水,瓶身的冰凉透过指尖,一直传到心里。
我没舍得立刻喝。
我把它放在搅拌机后面的一块砖头下,想着等最热的时候再喝。
那天下午,太阳格外毒。我感觉自己快要被烤化了,嘴唇干得裂开了口子。
我好几次都想去喝那瓶汽水,但都忍住了。
那一点冰凉和甜意,成了一种念想。光是想着它的存在,就觉得酷热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。
收工的时候,我才想起那瓶汽水。
我走过去,把它拿出来。瓶身上的水珠早就干了,被太阳晒得温热。
我拧开瓶盖,仰头灌了一大口。
没有想象中的冰爽,只有一股温吞的、甜得发腻的味道。
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还是觉得,那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汽水。
从那天起,我开始在干活的间隙,偷偷地看她。
她通常都坐在不远处的一棵槐树下,那里有个小马扎。她手里总捧着一本书,看得格外认真。
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点。风一吹,光点就在她身上跳跃。
我看不清她看的什么书,但我知道,那一定是一个和我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一个没有水泥、没有沙子、没有汗臭的世界。
有时候,她会抬起头,目光朝工地的方向望过来。
每当这时,我就会立刻低下头,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。我假装专心致志地和面前的水泥搏斗,用尽全力挥舞着铁锹,仿佛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倾泻出去。
我希望她能看到我的努力。
又或者,我希望她根本不要看到我。
这种矛盾的心理,像两股力量在我身体里拉扯。
和我一个工棚的李叔,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友。他是工地上资历最老的人,连王工头都要让他三分。
他看出了我的心思。
有天晚上,他递给我一支烟,说:“小子,别看了。不是一个道上的人。”
我没接他的烟,只是把头埋得更低。
“那姑娘,是金凤凰。咱们这,是泥瓦窝,留不住的。”李叔拍了拍我的肩膀,叹了口气。
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。
可道理是道理,心里的感觉,却不是道理能管得住的。
我开始利用休息时间,偷偷看书。
那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本旧诗集,书页都泛黄了,边角也卷了起来。
我怕被人看见笑话,总是躲在工棚后面的一个角落里看。
有一次,我正看得入神,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。
“你也喜欢看书?”
我吓了一跳,手里的书差点掉在地上。
是她。王静。
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。
我慌乱地把书往身后藏,脸涨得通红,像被火烧一样。
“我……我随便看看。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
她没有笑话我,反而蹲了下来,好奇地看着我手里的书。
“能给我看看吗?”
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把书递给了她。
她接过去,小心地翻开,像是对待一件珍宝。
“是泰戈尔的诗。”她轻声说,“我中学的时候也读过。”
“你……你也喜欢?”我鼓起勇气问。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,“‘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’,我最喜欢这句。”
阳光照在她长长的睫毛上,投下一小片阴影。
那一刻,我感觉周围搅拌机的轰鸣、工友的叫喊,全都消失了。
我的世界里,只剩下她轻柔的声音,和空气中那股淡淡的、好闻的皂角香。
从那以后,我们偶尔会说上几句话。
她会问我老家是什么样子,问我山里的事。
我跟她说,我们那里的天特别蓝,云特别白,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,像撒了一把碎钻石。
我跟她说,夏天的时候,山里的溪水冰凉刺骨,把西瓜放在里面镇半个小时,拿出来比冰块还解暑。
我说这些的时候,她总是听得特别认真。
她的眼睛亮晶晶的,仿佛能看到我描述的画面。
“真好。”她总是这么说。
而我,也从她那里,知道了另一个世界。
我知道了什么是图书馆,知道了什么是音乐会,知道了城里有一种叫“咖啡”的东西,是苦的,但很多人喜欢喝。
我们的交流,像两条从不同源头流出的小溪,偶然间交汇在了一起。
虽然我们都知道,它们最终会流向不同的方向。
但那短暂的交汇,已经足够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欣喜。
然而,好景不长。
王工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。
他看我的眼神,变得越来越不对劲。
以前,他只是骂我手脚慢。现在,他开始变着法地挑我的刺。
“这灰浆拌得太稀了!你想偷懒省水泥是不是?”
“让你去搬砖,你耳朵聋了?”
“你那是什么眼神?不服气?”
他把最重最累的活都派给我,还总是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。
工友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。有同情的,有幸灾乐祸的,也有疏远的。
李叔又找过我一次。
“小子,听叔一句劝,离那姑娘远点。王阎王这是在敲打你呢。”
我沉默着,把拳头捏得咯咯作响。
我知道王工头是故意的。
他想让我知难而退,想让我像只苍蝇一样被他挥手赶走。
我心里憋着一股气。
这股气,让我干活更卖力了。
我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,都化作了力气,发泄在那些水泥和砖块上。
我像一头憋着劲的牛,只知道低头往前冲。
我想证明,我不是他想的那种人。我不是想攀高枝,我只是……我只是想和她说几句话而已。
就这样,在压抑和煎熬中,到了发工钱的日子。
工地上的人,都盼着这一天。
这是他们用汗水和力气换来的希望,是家里老婆孩子的生活费,是老家父母的医药钱。
工人们排着队,挨个从王工头手里接过一个信封。
拿到信封的人,都会躲到一边,小心翼翼地打开,把里面的钱一张一张地点好几遍,脸上的表情,是疲惫里透着满足。
轮到我了。
我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伤口的手。
王工头看了我一眼,眼神里带着一丝轻蔑。
他没有给我信封。
他从一沓钱里,抽出几张,扔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。
那几张钱,比我应得的,少了一大半。
“你这个月,好几次偷懒耍滑,这钱,是扣你的。”他声音不大,但周围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
我能感觉到那些目光,像针一样,扎在我的皮肤上。
我的血,一下子全涌到了头顶。
耳朵里嗡嗡作响,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偷懒耍滑?
我一个月下来,磨破了两双手套,鞋子前面都张了嘴。我每天干的活,比谁都多,比谁都重。
现在,他当着所有人的面,说我偷懒耍滑。
这比用鞭子抽在我身上还难受。
“工头,我没有。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。
“我说你有你就有!”王工头把眼睛一瞪,“怎么,还想跟我犟嘴?”
“我干了多少活,大家伙都看着呢!你可以扣我的钱,但你不能这么说我!”我梗着脖子,一字一句地说。
“嘿!你小子还来劲了!”王工头一拍桌子,站了起来,“就给你这些!爱要不要!不要就滚蛋!”
周围的工友们,没有一个敢出声。
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,眼神复杂。
我看着桌上那几张被揉得皱巴巴的钱,又看了看王工头那张蛮横的脸。
一股热流从胸口直冲喉咙。
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。
我像一头驴,被人蒙着眼睛拉磨,拉得浑身是伤,最后连草料都被克扣了。
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?
为了那点可怜的工钱?还是为了那个遥不可及的、虚无缥缈的梦?
我深吸了一口气,胸腔里那股翻腾的火气,慢慢地沉了下去,变成了一块冰冷的铁。
我没有再看那几张钱。
我转过身,走到堆放工具的角落,拿起那把我用了几个月的铁锹。
然后,我走向我的工棚,从枕头下摸出我那个破旧的帆布包,把那本诗集和几件换洗的衣服塞了进去。
做完这一切,我背上包,扛着铁锹,头也不回地朝工地大门口走去。
钱我不要了。
人得要脸。
我能感觉到,身后所有的目光都追随着我。
我把腰杆挺得笔直。
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狼狈。
就在我一只脚即将迈出工地大门的时候,一只粗糙的大手,用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是李叔。
“别走。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。
我回过头,看着他。
他的脸上,满是焦急。
“叔,你别拦我。这地方,我待不下去了。”我平静地说。
“你不能走!”李叔加重了手上的力气,把我往回拽,“有人正等你。”
我愣住了。
等我?
谁会等我?
“你小子,就是脾气太犟。”李叔把我拉到一边,压低了声音,“王阎王他……他那是故意在试你。”
“试我?”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“有这么试人的吗?他那是把我当猴耍!”
“你懂什么!”李叔瞪了我一眼,“你以为你跟小静那点事,他看不出来?他闺女的心思,他能不知道?”
我的心,猛地一沉。
“他……他知道?”
“废话!全工地的人都快看出来了,他能是瞎子?”李叔说,“他今天这么做,就是想看看你的反应。你要是拿了那点钱,忍气吞声地留下,他瞧不起你。你要是跟他大吵大闹,撒泼打滚,他也瞧不起你。”
我呆呆地听着,脑子一片空白。
“他就是想看看,你小子到底有没有骨气。现在,你扛着铁锹要走,对了!这才是他想看到的!”李叔的语气里,竟然有几分兴奋。
“你跟我来。”
李叔不由分说,拉着我的胳膊,就往工地里头的一排平房走去。
那是王工头的办公室兼住处。
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,迈不动步。
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麻。
这一切,都是一个局?一个专门为我设下的局?
这太荒唐了。
我只是一个扛水泥的,我有什么值得他这样大费周章?
“叔,我不去。”我挣扎着想停下。
“怂什么!”李叔回头呵斥道,“都到这节骨眼了!小静还在里头等你呢!”
小静……王静……
她也在等我?
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。
我不再挣扎,任由李叔拉着我,走到了那扇绿色的木门前。
门虚掩着。
李叔在门上敲了敲,然后把我往前一推。
“进去吧。”
他自己却没有进来,转身走了。
我站在门口,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暗,窗帘拉着。
一张办公桌,几把椅子,一个铁皮文件柜。陈设很简单。
王静就坐在桌子后面的一把椅子上。
她没有看书。
她只是安静地坐着,双手放在膝盖上。
看到我进来,她站了起来。
“你……”
“我……”
我们两个同时开口,又同时停住。
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沉默。
我能听到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声。
还是她先开了口。
“我爹他……你别怪他。他就是那个脾气。”她的声音很低,带着一丝歉意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只能傻站着。
“他就是想看看……看看你是不是一个能担当的人。”她抬起头,看着我,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。
“担当?”我苦笑了一下,“我一个扛水泥的,能担当什么?”
“不是的。”她摇摇头,很认真地说,“我爹说,一个人穷不要紧,但不能没骨气。一个人力气小不要紧,但不能没担当。”
她顿了顿,继续说:“他都看到了。你每天干多少活,他心里有数。你偷偷看书,他也知道。”
我的心又是一震。
原来,我以为的那些秘密,在他的眼皮子底下,根本无所遁形。
“我……我只是……”我想解释,却发现语言是那么苍白。
“你别说了,我懂。”她打断了我。
“你先坐。”她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。
我依言坐下,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。我甚至能感觉到,我裤子上的灰尘,正在簌簌地往下掉。
她给我倒了一杯水。
是那种带花纹的玻璃杯,很干净。
我双手接过来,杯子里的水有些烫。
“我跟我爹说,我想继续上学,考大学。”她突然说。
我抬起头,有些诧异地看着她。
“他不同意。他说女孩子家,读那么多书没用,早晚要嫁人。”她的语气里,透着一丝无奈。
“他说,除非我能找一个他也看得上的人。那个人,可以没钱,但一定要有志气,有上进心。”
她说到这里,停了下来,看着我。
我的呼吸,几乎停止了。
我再迟钝,也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。
我的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,像是炸开了一颗炸弹。
这……这怎么可能?
我何德何能?
我只是一个从山沟里出来的穷小子,一个在工地上出卖力气的苦力。
而她,是工头的女儿,是那只高高在上的金凤凰。
我们之间,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“你……你为什么……”我艰难地开口,声音嘶哑。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轻轻地摇了摇头,目光飘向窗外,“可能是因为,你跟他们不一样吧。”
“那天,我看到你在角落里看书。那么吵,那么乱,你却能看得那么专注。我觉得,你的心里,一定装着一个和这里不一样的世界。”
“后来,我听你讲你老家的山,老家的水。你的眼睛里有光。那种光,我爹有,但工地上其他叔叔伯伯没有。”
“那是一种……对未来的向往。”
我呆呆地听着。
原来,在我偷偷看着她的时候,她也在观察着我。
原来,我那些不为人知的心事,都被她看得清清楚楚。
“我爹今天这么对你,其实也是我的主意。”她低下头,声音更小了,“我想看看,你会怎么选。”
“如果你忍了,说明你没有血性。如果你闹了,说明你不够沉稳。”
“只有你现在这样,不卑不亢地离开,才是我心里想的那个人。”
我的心,像是被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抚摸着。
所有的委屈,所有的不甘,在这一刻,都烟消云散了。
原来,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原来,我所坚持的那些看似可笑的尊严和骨气,在另一个人的眼里,是如此珍贵。
就在这时,门被推开了。
王工头走了进来。
他没有看我,径直走到桌子前,拉开抽屉,拿出两个厚厚的信封,扔在我面前。
“一个是你这个月的工钱,一分不少。另一个,是奖金。”他瓮声瓮气地说。
然后,他抬起眼皮,扫了我一眼。
那眼神,不再是轻蔑和蛮横,而是一种复杂的、审视的目光。
“小子,我闺女看上你了,说你有出息。”
“我丑话说在前头。你想跟她在一起,光有骨气还不行。”
“你得干出个人样来给我看!”
“你要是敢让她受一点委屈,我打断你的腿!”
他说完,不再理我,转身对他女儿说:“饭做好了没?饿死了。”
王静的脸“唰”地一下红了,像天边的晚霞。
她瞪了他爹一眼,然后快步走进了里屋。
我坐在椅子上,看着面前的两个信封,感觉像在做梦。
一场离奇又真实的梦。
那天晚上,我没有回工棚。
王工头让我留下来吃饭。
饭菜很简单,两菜一汤,但有肉。
吃饭的时候,王工头一句话也没说,只是一个劲地喝酒。
我和王静,也沉默着。
饭桌上的气氛,有些古怪。
吃完饭,王工头指着里屋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对我说:“今晚你睡这。”
然后,他就回自己屋了。
我躺在那间小屋的床上,床板很硬,但被褥很干净,散发着阳光和皂角的味道。
是和她身上一样的味道。
我睁着眼睛,看着天花板,一夜无眠。
第二天,我没有再去工地扛水泥。
王工头让我跟着他,学着看图纸,学着算料,学着管理工地上的大小事务。
他说:“光有力气是蠢牛,有力气有脑子,才能成事。”
我学得很用心。
白天,我跟在他身后,像一块海绵,拼命吸收着所有我能接触到的知识。
晚上,我就在灯下,啃那些厚厚的建筑图纸和规范手册。
王静会给我泡一杯热茶,然后安静地坐在我对面,看她自己的书。
有时候我看得累了,一抬头,就能看到她。
灯光下,她的侧脸柔和得像一幅画。
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辛苦,都值了。
工友们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。
从最初的同情,到后来的嫉妒,再到最后的敬畏。
他们开始叫我“小王工”。
只有李叔,还像以前一样,拍着我的肩膀,叫我“小子”。
他说:“小子,有出息。叔没看错你。”
我和王静的感情,也在这种平淡而温馨的日常里,慢慢升温。
我们没有说过什么海誓山盟。
但有时候,一个眼神,一个微笑,就足够了。
有一次,我带她去了我刚来这个城市时站过的那个街口。
车来车往,人潮汹涌。
“我刚来的时候,就站在这里。”我对她说,“那时候我觉得,这个城市好大,大得能把人吞下去。”
她握紧了我的手。
“现在呢?”她问。
我转过头,看着她。
她的眼睛里,映着我的影子。
“现在,”我笑着说,“我觉得,这个城市再大,只要有你在,我就有家了。”
她的眼圈,一下子就红了。
两年后,我们结婚了。
婚礼很简单,就在工地的食堂里,摆了几桌酒席。
来的都是工地上最熟悉的叔叔伯伯。
王工头那天喝了很多酒,喝醉了。
他拉着我的手,一遍又一遍地说:“小子,我闺女,就交给你了。你……你可得对她好。”
我用力地点头。
我说:“爹,你放心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叫他“爹”。
他愣了一下,然后,这个在工地上说一不二的“王阎王”,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。
又过了几年,我们用攒下的钱,加上王工头的支持,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建筑公司。
我不再是那个只会扛水泥的穷小子,成了一名真正的管理者。
我跑项目,谈合同,管理施工。
王静则负责公司的财务和内勤。她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我们依旧住在城郊,但已经搬出了那排平房,住进了自己盖的楼房里。
有时候,开车经过我们最初相遇的那个工地,我会停下来,看一会儿。
那里已经盖起了一栋高耸的住宅楼,灯火通明。
我仿佛还能看到,当年那个光着膀子、浑身泥浆的少年,正埋头挥舞着铁锹。
还能看到,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姑娘,安静地坐在槐树下,手里捧着一本书。
时光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河,冲刷着一切。
但有些东西,却被沉淀了下来,刻进了骨子里。
比如那瓶温热的橘子汽水,比如那本泛黄的诗集,比如那把油亮的铁锹。
它们是我青春的印记,也是我爱情的起点。
前几天,我儿子问我,什么是爱情。
我想了很久。
我没有跟他讲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。
我只是告诉他,爱情,可能就是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午后,你浑身脏得像个泥猴,却有一个人,愿意为你递上一瓶干净的汽水。
然后,她会告诉你,她看到了你心里的光。
牛金所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